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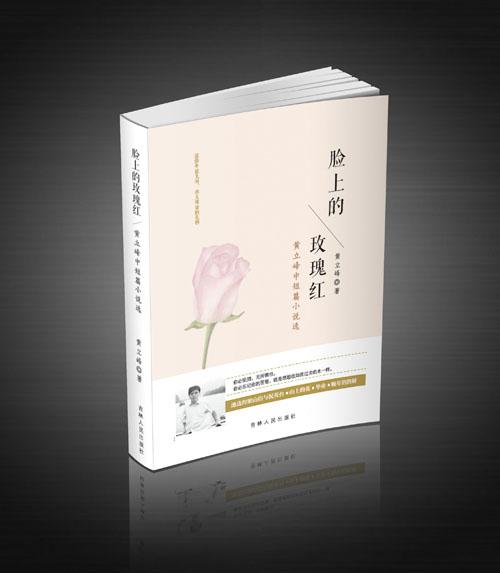
切入生活肌理,书写生存困窘——黄立峰《脸上的玫瑰红》
@解读晓章(教授、著名小说评论家)
作为一个六零后,黄立峰先生跟余华、苏童等名家是同时代人,而且差不多同时致力于小说创作。但是据作者自述,因为忙于生计,他所写的作品大都放入抽屉,成为“抽屉文学”了。直到近年,他才连着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《逃离与回归》,《千禧年》。在纯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,他的作品算是一种可贵的坚守,一种颇有创新精神的乡土叙事。
2017年7月,黄立峰的中短篇小说选《脸上的玫瑰红》,由吉林人民又出版发行了。
这是一部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品集,大部分作品写于新世纪初的几年。作者年逾不惑,思想阅历与叙述技巧都已趋于成熟。他的叙事风格,用该书出版社的评论,显得儒雅,内敛,接地气的。“平和的叙事中带着辛酸的幽默,带着一种智慧的反讽,粗看略显平淡,细品意味无穷。”“从这些作品中,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人生活的艰难与苦闷,有工厂转型时的荒诞与暴力,更多的是来自学校的无奈与挣扎。”就是说,黄立峰作品有三块被他成为“根据地”的土壤,学校,农村,远郊大厂。
我们打开《脸上的玫瑰红》,首先看到的就是作家书写学校的短篇《池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校园生活书写。作者从容不迫地叙述一个儿童溺水的故事。然后又不厌其烦地讲述事故发生以后,学校与受害人家属的讨价还价。最后又回到开头,在平静的叙述中,让读者痛惜一个生命的消失,感叹人生无常,生命低贱。
作家王安忆曾经这样比喻小说,说短篇小说是一种走在刀刃上的艺术,它非常危险,非常容易格式化,写作者非常容易跳进自己设定的窠臼里去。王安忆说好的小说会巧妙绕过窠臼,好像有一种魔力。反复阅读《脸上的玫瑰红》,就像高尔基说的读福楼拜的《一颗纯朴的心》,总是觉得作者那种不慌不忙的叙述中,有一种特别的魔力,让人掩卷之余,回味不已。我觉得黄立峰在书写校园生活时,总是选取与众不同的角度,例如《海龟》《不许作弊》《彩旗飘飘》,选集中每一篇各不相同。作者力图做到不重复自己,又不违背生活的逻辑。这里有一种穿透生活与教育本质的目光。学校本是培养人的地方。但是透过表面现象,我们看到了一些压制、摧残人的环节、制度或者校规。作家有他特殊的敏感,从孩子内心世界的角度,去发现并表现那些不合理与窘境,就有了思想深度,有了艺术的逻辑。
与校园题材相比,集子中写农村的作品,更显示作者的功力。世纪之交的农村,有一种人所共知的衰败,退化。作者无意给它唱一支挽歌,因而又选取特定的角度,来书写农民的种种生存困境。《桑榆》写的是一个老人,家里有四个早已成家立业的儿子。老人很孤独,想进敬老院,去求四个儿子答应。结果四个儿子一一拒绝他。他最终选择了自杀,几个儿子给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。
《桑榆》反应的是一个社会问题。也是新时期公益事业兴起以后的新问题。各地办起了公益性质敬老院,孤寡老人得到了安排。然而有子女的老人,想进敬老院却会遭到家庭的反对。这里涉及到养老观念问题。农村里普遍不能接受有子女的老人进养老院。于是才有了《桑榆》中这样的悲惨故事。
另有一篇《喜庆日》,更是一个奇特的篇章,写的是特别要面子的底层人士,因为邻居书记家嫁女没有叫他,由憧憬,到失落,到最后愤怒绝望,喝酒解愁,直到喝农药把自己毒死。一个说来荒谬的故事,作者写得从容不迫,有板有眼,把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刻画得细致入微,因此读来变得真实可信。这是一种符合生活逻辑的艺术真实。
当然,除了写这种近乎黑暗的生存窘迫,作者也有比较富于亮色的篇章,例如《老七的方向盘》《好人阿土》等。写农村中的热心人,老实人,写他们的生生死死,喜怒哀乐。
作者写远郊大厂的篇目较少,只有两个短篇,两个小小说。短篇《写真》《人心》,写的是工厂转型时的特殊时事,改革给国营企业工人带来的冲击,要大于散兵游勇的农民。由此产生那种近乎荒诞的剥衣报复,以及凶杀暴力,都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。事迹见证一个时代,小说挖掘当时人的内心。
除此之外,集子中的小小说,都极有特色,值得一读。这里限于篇幅,不一一细说。集子后面两部中篇小说,叙述技巧与思想内涵,都值得探究,日后再谈。 |